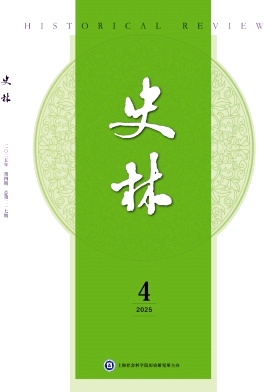| 226 | 0 | 170 |
| 下载次数 | 被引频次 | 阅读次数 |
鸦片战争前,华官与在粤英官就中英命案法权问题持续斗争百余年。1689年中英第一起命案发生。18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萌生夺取中国对华英命案的法权之恶念。在粤英官通过1784年“休斯夫人号案”明确抵抗中国法权,1800年“朴维顿号案”强行参与中国法权,1807年“海王星号案”分解中国法权,1810年“黄亚胜案”逃脱中国法权,及至1839年又通过“林维喜案”彻底侵夺中国法权。在上述不同性质的华英命案交涉中,先是广州夷馆英官、英国海军官员共同谋夺华官对港脚商船、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英国兵船所涉命案之法权,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散局后,同华官争夺法权的英官,由公司大班、兵舰舰长演变为直接代表英国政府的“贸易监督”。以上主体合力最终攫取到在华“事实上的治外法权”。这表明在鸦片战争前,广州已沦为英国“有域外管辖权之地”,中国独立的司法主权已遭到严重侵蚀。
Abstract:The present paper,looking back at homicide cases,such as the cases involving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s Guangzhou factory( 1689),British ships Lady Hughes( 1784),Providence( 1800),Neptune( 1807) and so on,and the Huang Yasheng and Lin Weixi cases as well,concludes that the British empire had obtained de facto extraterritoriality,Guangzhou had been reduced to a place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Chinese law,and China's independent judicial sovereignty had been severely eroded.
(1)照吴颂皋所言,“凡在国家境内之人与物,概须受该国法律的管辖,是谓法权”,据此本文所谓“法权”主要指管辖权。参见吴颂皋:《治外法权》,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5页。所谓“治外法权”,曾指一国所派外交人员不受所在国管辖的特权。在近代中国语境内,主要指西方列强在华本国侨民不受中国管辖的特权(参见屈文生:《从治外法权到域外规治——以管辖理论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殖民话语与近代英美在华“管辖权政治”》,《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本文所指“法权”与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无涉。后者实为某种“民事权利”,与管辖权、特权无关。参见陈中绳:《关于废除“法权”译名的建议》,《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徐国栋:《Das bürgerliche Recht在中国:从“资产阶级法权”到“民事权利”——民法从不平等的体现到平等的体现逆转史》,《法律与伦理》2022年第2期。
(2)另两类命案,即华人杀毙英人和英人相杀及英人与他国人相杀案件,前者因华官通常秉公适用《大清律例》,且多依“一命一抵”追究华人刑事责任,故英人无异议,不会成为争议问题;后者因属西人相犯案件,华官往往以“怀柔远人”之名,交洋官自行处断,故华人无异议,也不会成为需要双方交涉的问题。
(3)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523—524页。
(4)策楞本件题奏,属于先斩后奏。皇帝同意策楞题奏中秉持的“一命一抵、情罪相符”原则,认为“夷目眼同尸亲将宴些卢勒毙”合理得当,“应毋庸再议”。参见《澳门记略·一件奏明事札付》(1744年,月日不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六),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291页。
(5)梁廷枏著,袁钟仁点校《粤海关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10—511页。
(6)《广州将军策楞等奏报办理晏些卢扎伤商人陈辉千致死案缘由折》(1744年2月27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7)所谓“化外人”者,“凡外国来归之人,散处各地方者皆是”。参见陈颐、解锟点校《大清律例源流汇考》第2册,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463页。
(8)参见《广州将军策楞等奏报办理晏些卢扎伤商人陈辉千致死案缘由折》(1744年2月27日),《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第199页。
(9)“著为令”的过程是立法过程。参见万明:《明令新探——以诏令为中心》,杨一凡主编《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2页。
(10)参见《大清律例重订统纂集成》卷5《名例律下》,道光十年醉经楼刻本,第54页。另见《澳门记略·一件奏明事札付》(1744年,月日不详),《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六),第290—291页。以上文献所录文字略有差异,本处引文采用《大清律例重订统纂集成》。下划线为引者所加。
(11)参见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109页。一般而言,由皇帝诏旨御准的司法程序,通常会经刑部律例馆收集编纂为“例”,使其成为具有普遍约束性的法律规范。但“乾隆九年定例”仅适用于澳门一地,因此未被编入《大清律例》。参见D.布迪、C.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12)参见屈文生:《1807年中英“海王星号案”与英国在华“事实上的治外法权”》,《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
(13)参见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第111—112页。
(14)东波塔档案内有“陈亚连案”12件往来档案,参见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澳门基金会1999年版,第337—342页;另见刘景莲:《明清澳门涉外案件司法审判制度研究(1553—1848)》,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251页。
(15)译自葡文Senado da Camara de Macau,英文为Town/Municipal Council;也称澳门“议事公局”,设于1583年。盖受此名谓影响之缘故,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夷馆在18—19世纪时也常被称作“公局”。二者职能虽有些类似,但性质大相径庭。
(16)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41页。
(17)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黄鸿钊、李保平译,澳门基金会2000年版,第164页;何志辉:《明清澳门的司法变迁》,澳门学者同盟2009年版,第176—180页;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9页。
(18)在葡官同华官争夺法权过程中,也有被告人为英国人的命案,如1772年“刘亚来案”。见龙思泰著,章文钦校注《早期澳门史》,吴义雄、郭德焱、沈正邦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99页;艾德华:《清朝对外国人的司法管辖》,李明德译,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增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466页。
(19)有学者列出了1807年前的澳门命案12件,参见刘景莲:《明清澳门涉外案件司法审判制度研究(1553—1848)》,第228—230页。
(20)清朝于1683年收复台湾后,次年即开海禁。清中前期“四口通商”时代共73年(1685—1757),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后设于松江府,又移驻上海县)四口各自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1757年后,清朝进入长达85年的广州“一口通商”时代(1757—1842)。因此,鸦片战争前内地中英法权问题主要集中于广州法权争夺之上。
(21)基顿(George Williams Keeton)引用马士著作,将案件发生地误作澳门,但马士在其书中皆作广州。苏亦工引用基顿书时,将案件发生地照录为澳门。参见伟烈亚力口译,王韬笔受《华英通商事略(1857年)》,屈文生、万立编《王韬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43页;苏亦工:《中法西用——中国传统法律及习惯在香港》(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George Williams Keeton,The Development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Vol.1,London:Longmans,Green & Co.,1928,p.29;H.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London:Longmans,Green & Co.,1910,p.101。
(22)1716年后,公司董事会决议放弃其他在华“据点”,集中在广州商馆开展对华贸易。
(23)Peter Auber,China:An Outline of Its Government,Laws,and Policy,and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Embassies to,and Intercourse with,that Empire,London:Parbury,Allen and Co.,1834,pp.152-154.
(24)H.B.Morse,“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Central Asian Society,Vol 10,no.2 (1923),pp.123-138;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Vol.1,Oxford:Clarendon Press,1926,p.193.
(25)George Williams Keeton,The Development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Vol.1,p.31.
(26)17世纪末,外商船只在驶入广州前常先泊于澳门,同当地华民交易,其多数出口商品来自广州。澳门受广州府管辖。参见范岱克:《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江滢河、黄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
(27)在澳门法权问题中,同华官争夺管辖权的主要是澳门议事会或澳督等葡国在澳自治机关。在广州法权问题中,同华官争夺管辖权的主要是东印度公司广州“据点”,即夷馆或称商馆特选委员会主席等英官,经常谓之“大班”。
(28)George Thomas Staunton,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 and our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at Country,including a Few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London:John Murray,1850,p.333.
(29)《华英通商事略(1857年)》,屈文生、万立编《王韬卷》,第48页。
(30)参见陈利:《法律、帝国与近代中西关系的历史学:1784年“休斯女士号”冲突的个案分析》,邓建鹏、宋思妮译,《北大法律评论》第12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3页。
(31)中方向来认为港脚商船该由公司大班负责,而英官向来推脱责任。例如,1781年英国港脚船“达多劳号”(Dadoloy)公然抢劫停泊澳门的一艘荷兰货船,案件发生后,广东巡抚李湖令公司大班罢剌查(James Bradshow)等交还荷兰货船,并指出“尔等既充大班、二班,尔国王派尔等来料理公班衙船事务……尚且要管束他。那[哪]有港脚船的夷人,倒不听你们的说话?”见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36页。
(32)事实上,《大清律例》区别故杀和过失杀。清代对杀人罪有谋杀、故杀、劫杀、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之分。
(33)《华英通商事略(1857年)》,屈文生、万立编《王韬卷》,第48页。
(34)George Williams Keeton,The Development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p.42.
(35)与1784年“休斯夫人号案”不同,1800年“朴维顿号案”成为英方拒不交出罪犯的首案,而1807年“海王星号案”成为英方行使会审权的首案。在1810年“黄亚胜案”、1822年“土巴资号案”、1839年“林维喜案”等中英命案交涉中,英国再未交出凶手。
(36)所谓“有域外管辖权之地”,即指“英国女王陛下拥有权力和管辖权的、女王陛下属地之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参见 “An Act to Remove Doubts as to the Exercise of Power and Jurisdiction by Her Majesty within Divers Countries and Places out of Her Majesty’s Dominions,and to Render the Same More Effectual,24th August 1843,” in N.Simons ed.,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Vol.16,London:George E.Eyre and Andrew Spottiswoode,1843,p.927。
(37)关于本案详情叙事,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1册,第536—539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2卷,区宗华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9—379页。
(38)《粤督抚海关因英船命案下行商谕》,许地山编《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文物出版社2022年版,第208—209页。此前公司也有过类似推脱,认为港脚船不归其管,现又提出兵船不归其管,皆是为了阻挠中方行使法权。
(39)许地山编《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第209—211页。
(40)参见小斯当东初到广州后,就本案向其父亲老斯当东所做的长篇报告。“Letter to George Leonard Staunton,27 March 1800,Canton,” in China Through Western Eyes Manuscript Records of Traders,Travellers,Missionaries & Diplomats,1792-1942,Part 2,Reel 27;John Francis Davis,History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Vol.1,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36,p.80.
(41)Caroline Stevenson,Britain’s Second Embassy to China:Lord Amherst’s “Special Mission” to the Jiaqing Emperor in 1816,Acton: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21,p.39.另参见萧致治、杨卫东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5页。
(42)参见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2卷,第377页。
(43)此六条的原文及译文,参见Chen Li,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Sovereignty,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6,p.96;许地山编《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第211页。
(44)有学者认为,“朴维顿号案”的恶性在于开中英会同审理之先例,标志着清朝的司法主权遭到破坏。此说不确。参见萧致治、杨卫东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第264—266页。
(45)关于本案更为详细的介绍,参见屈文生:《1807年中英“海王星号案”与英国在华治外法权之事实攫取》,《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
(46)Ta Tsing Leu Lee,Being the Fundamental Laws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Supplementary Statutes 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trans.by George Thomas Staunton,London:Cadell and Davies,1810,p.515.
(47)“交禁解勘”是指将犯人移交关押并押送上级官府复审的程序,其中,“交”即移交、交付;“禁”指监禁、关押;“解”即押送;“勘”指复核、审查。
(48)顾维钧:《外人在华之地位》,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36页。
(49)George Thomas Staunton,“Considerations upon the China Trade,” in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ed.,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 and our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at Country,including a Few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Street,1822-1850,p.134,footnote.
(50)在小斯当东看来,对于清政府而言,嘉庆皇帝关于“海王星号案”的这道谕令传递出的负面信息,远甚于记录在案的几乎任何一部公开立法。但小斯当东同时试图说明:根据广州通商口岸的习俗,行商对闹事水手所属船舶负概括性责任(general responsibility,即连带责任),据说该行商花了将近5万英镑收买有关各方,为的是确保利益相关方默不作声。必须承认的是,证人和在场的其他主体都受到了超乎寻常的诱惑,而这种诱惑,在任何国家或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很少能够禁得住。Ta Tsing Leu Lee,Being the Fundamental Laws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Supplementary Statutes 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p.516.
(51)Peter Auber,China:An Outline of its Government,Laws,and Policy,and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Embassies to,and intercourse with,that Empire,p.228.另参见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小斯当东回忆录》,屈文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4页。
(52)参见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Vol.3,Oxford:Clarendon Press,1926,pp.123-126,155-156;冷东、沈晓鸣:《黄亚胜案件辨析》,《学术研究》2014年第12期;冷东、沈晓鸣:《嘉庆年间英国水手刺死中国人黄亚胜案》,《历史档案》2014年第2期;冷东、吴东艳:《黄亚胜档案与清代文书制度》,《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等。
(53)此“亚士但”系英国著名作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胞兄。
(54)《喇佛上两广总督禀》,许地山编《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第118页。
(55)《南海县下洋商谕》,许地山编《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第126—130页。
(56)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Vol.3,p.155.
(57)《广东巡抚为黄亚胜被夷人戮伤身死事下南海县札》,许地山编《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第106页。
(58)《粤海关下洋行商人谕》,许地山编《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第115页。
(59)关于“土巴资号案”详情,参见马礼逊:《伶仃案纪实》,艾丽莎·马礼逊编《马礼逊回忆录》(下),杨慧玲等译,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第705—725页;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第92—98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4卷,第21—22页。
(60)以上各情节,参见《两广总督阮元奏报英国护货兵船伤毙民人畏罪潜逃饬令交凶折》(1822年2月19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164页;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30—34页。
(61)参见《两广总督阮元奏究办英吉利凶夷伤毙内地民人一案情形折》(1823年9月24日),《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98—99页。
(62)一般刑事案件,清政府主要督饬外国人自行处置,而非直接审判处罚。参见王巨新:《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研究——以广东地区来华外国人管理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5页。
(63)马礼逊:《伶仃案纪实》,艾丽莎·马礼逊编《马礼逊回忆录》(下),第283页。
(64)早于“士巴资号案”两个多月,在1821年9月23日中美“特拉诺瓦案”中,阮元在案发一个月后就派人带走了犯事水手佛兰西士爹剌那非了(Francis Terranova,今译“特拉诺瓦”“泰拉诺瓦”等),其最终被中方绞决。可见,美国在华官员相较英官无力争夺广州法权。关于“特拉诺瓦案”各情形,参见William J.Donahue,“The Francis Terranova Case,” Historian,Vol.43,no.2 (1981),pp.211-224;王元崇:《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文汇出版社2021年版,第133—160页;李秀清:《中美早期法律冲突的历史考察——以1821年“特拉诺瓦案”为中心》,《中外法学》2010年第3期等。
(65)1836年起接替罗便臣(Sir William Robinson)担任英国驻华商务正监督的义律,是英国驻华级别最高的行政官员,完全有别于东印度公司时代的“大班”。义律在与华官往来的禀文中常自称“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等。
(66)关于“林维喜案”,参见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第129—142页;林启彦、林锦源:《论中英两国政府处理林维喜事件的手法与态度》,《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廖伟章:《林则徐在交凶问题上与义律的斗争》,《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67)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30页;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戦争前中英交涉文書』、嚴南堂書店、1967年、219—220頁。
(68)常昌盛、谢庆立:《〈中国丛报〉报道与“林维喜案”中的领事裁判权问题》,《新闻爱好者》2022年第12期。
(69)《义律海军上校致巴麦尊子爵函》(1839年8月27日),《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胡滨泽,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30页;William Travis Hanes III and Frank Sanello,The Opium Wars:The Addiction of One Empire and the Corruption of Another,Naperville:Sourcebooks,2002,p.62.
(70)参见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戦争前中英交涉文書』、220頁。
(71)参见林启彦、林锦源:《论中英两国政府处理林维喜事件的手法与态度》,《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72)郭卫东:《近代中国利权丧失的另一种因由——领事裁判权在华确立过程研究》,《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73)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215页。
(74)A Digest of the Despatches on China (including Those Received on the 27th of March) with a Connecting Narrative and Comments,London:James Ridgway,1840,p.125.
(75)林则徐组织翻译,伯驾、袁德辉各译出其中片段。参见万立:《从万国法到国际法——清季国际法翻译与国际法历史主义转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76)《会批澳门厅转禀义律抗不交凶说帖》(道光十九年七月初九日),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9—130页;林则徐全集编写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10册《译编卷》,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134页。
(77)林启彦、林锦源:《论中英两国政府处理林维喜事件的手法与态度》,《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坚持不放弃完整的司法主权,并向道光帝提出“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等治理中西关系的原则,惜未得到朝廷重视。然道光朝伊始,清廷在一些情形中已放松对外人的管理,如华官在道光元年“土巴资号案”中同意英国“自行正法”。参见《林则徐等奏英人仍图卖鸦片并予断绝贸易折》(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246页。
(78)《廷寄·答林则徐等折》(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243页。
(79)义律设立兵舰法庭并举行审判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执行英国政府1833年颁布的枢密令。参见万立、屈文生:《近代英国对华域外法体系研究》,《中外法学》2021年第5期。
(80)英国对华贸易的主体主要为持有英王特许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和“港脚商人”(country-traders)。“港脚商人”所驾商船即为“港脚商船”(country-trading ship)。“港脚”二字系country一词的音译。“港脚商人”与“散商”(private traders)的内涵不完全相同。
(81)船舶的性能、载重等物理属性对中英法权交涉也会产生影响,但并不重要,此处不予讨论。
(82)王韬和伟烈亚力于1857年合译出一篇重要文献《华英通商事略》。其叙事起点是英王伊丽莎白一世遣使访华的1596年,止笔于1834年。是年,东印度公司在华垄断贸易告终。其较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五卷本的出版早53年,虽非一部详细的中英通商通史作品,但对于了解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史仍有价值。
(83)参见高志:《澳门与英国人(1637—1842):香港的前奏》,叶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
(84)Kate Miles,“‘Uneven Empires’:Extraterritoriality and the Early Trading Companies,” in Daniel S.Margolies et al.eds.,The Extraterritoriality of Law:History,Theory,Politics,London:Routledge,2019,p.97.
(85)参见高志:《澳门与英国人(1637—1842):香港的前奏》,第75页;韩洁西:《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三个苏格兰人与不列颠全球帝国的崛起》,史可鉴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3页。
(86)Yukihisa Kumagai,“The Making of the ‘Free Trade Nation’:The Opening of the East India Trade and the British Manufacturing Industry,1790s-1830s,” The Economic Review of Kansai University,Vol.67,no.4 (2017),pp.673-693.
(87)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1册,第540页。
(88)参见汪熙:《约翰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6、347页;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Vol.1,Oxford:Clarendon Press,1926,p.15.
(89)Kate Miles,“‘Uneven empires’:Extraterritoriality and the Early Trading Companies,” in Daniel S.Margolies et al.eds.,The Extraterritoriality of Law:History,Theory,Politics,pp.97-98.
(90)参见唐伟华、黄玉:《清代广州涉外司法问题研究(1644—184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9页。
(91)到1807年“海王星号案”发生前后,保商仍约有12家。参见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续考》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2、59、64、75、101、107、283、296、299页;另参见《潘启官等九行商致特选委员会商请公班衙较往年早些上省携带压核扇同来函》(1807年9月6日)。见《潘启官等行商致特选委员会促其禀呈总督承诺将英人凶嫌压核扇尽速带回省城受审》,吴义雄主编《清代广州口岸历史文献丛编》(第一辑第二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4—36页。
(92)参见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30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六),第148页。
(93)James Cable,Gunboat Diplomacy,1919-1991:Political Applications of Limited Naval Force,London:Macmillan,1994,p.14.
(94)Superintendent起先译作“贸易监督”,这一译名一度为“领事”取代,在《南京条约》中亦译为“领事”。这也是1834年后到《南京条约》订立前后的中文档中,同华官抢夺治外法权的英官主体,在中文档案中皆为“英吉利国领事”的原因。中美《望厦条约》第一次将consul同今日使用之“领事”对应起来,此后中英中美条约文本中的“领事”,概译自consul。质言之,鸦片战争前,中文档案中,凡“英吉利国领事”,实指“贸易监督”。
(95)Peter Auber,China:An Outline of its Government,Laws,and Policy,and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Embassies to,and Intercourse with,that Empire,p.410.
(96)Peter Auber,China:An Outline of its Government,Laws,and Policy,and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Embassies to,and Intercourse with,that Empire,p.412.
(97)原文为:“….that the title of superintendent should be changed to consul,in whom should be vested all the powers exercised by the former”,参见顾维钧:《外人在华之地位》,第60页。
(98)1780—1782年任广东巡抚的李湖有如下判断:“外洋各国夷人来广贸易,都是安分守法。唯尔英吉利国夷人,往往逞强滋事。”《鸦片战争》第1册,第36页。
(99)关于“完整的领事裁判权”“不完整的领事裁判权”,以及英国在华“行使”治外法权主体的演变,参见屈文生:《英美在近代中国行使治外法权主体之型化与形替》,《法学研究》2023年第3期。
(100)东印度公司广州夷馆1834年的散局促成1843年治外法权从一种事实上的“特权”(privilege)转变为一种条约上的“权利”(right),并最终使得治外法权转变为一种殖民帝国对近代中国的羞辱与惩罚。参见Kate Miles,“‘Uneven Empires’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the Early Trading Companies,” in Daniel S.Margolies et al.eds.,The Extraterritoriality of Law:History,Theory,Politics,p.95。
基本信息:
DOI:
中图分类号:D929;D956.1;K249;K561.43
引用信息:
[1]屈文生.鸦片战争前的中英法权问题[J].史林,2025,No.216(03):33-48+217.
基金信息:
浙江大学“重要国家区域研究专项”“英美殖民帝国在华治外法权研究”阶段性成果;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